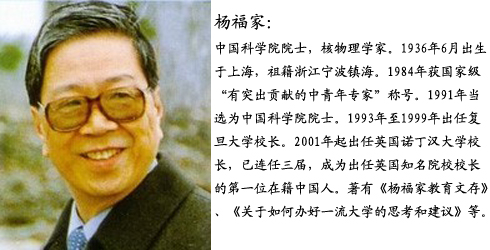
• 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。
• 英国大学高明之处在于实行导师制,每个人从进大学起就有人关爱。
• 现代大学四要素:有形资产、人力资源、文化内涵、良好办学机制。
• 英国大学可以与美国竞争,但是永远超不过美国。
• 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。
• 大学可以抚育公司,却不应占有公司。
• 教授不一定当官,但要有发言权,受人尊敬。
什么是大学?
【《财经》记者 马国川】记者: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批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,温家宝总理也在一些场合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,而且直言对我国教育现状有一种危机感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杨福家:其实温总理已经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。2007年5月14号,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说:“一所好的大学,不在高楼大厦,不在权威的讲坛,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,而在于自己独特的灵魂,这就是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要通过讨论与交流,师生共进,教学相长,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,并不断完善和发扬,影响越来越多的人。这样,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,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,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。”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。
记者:如何具体化呢?
杨福家: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。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,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,即弄清楚什么是大学,或者说一所大学要有哪些基本要素?第一,要有“有型资产”,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大楼”的含义更全面,还包括设备、图书等等;第二,要有“人力资源”,包括“大师”。“大楼”、“大师”的说法来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,他说过:“所谓大学,非大楼之谓也,乃大师之谓也。”这个说法不完整,并不是梅贻琦先生讲得不完整,因为他不是回答“什么是大学”这个问题的,梅贻琦讲这句话的背景,1931年清华大学在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,学校已把重点放在引进大师上,而不是过多地关注房子,于是他强调大师的重要性。
除了大师,人力资源还包括优秀的教师、学生与管理人员。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,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授指导下,在人文、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,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,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,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要而充分的条件。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,晚上10点,仍有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科研。我深有感慨,难怪剑桥大学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在世界一流大学,这种情景到处可见。有“中国居里夫人”之称的吴健雄教授曾经说过: “什么叫一流大学?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”!确实,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,我们一定能看到,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,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授指导下、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日日夜夜地在探索自然的奥秘,攻克技术难关。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!
记者:一所大学除了“有型资产”和“人力资源”,还需要什么?
杨福家:还要有“文化内涵”,就是要有大爱,包括爱师、爱生、爱国家、爱世界等等,这是学校的一个关键所在。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。例如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“思想战胜权威”,前校长萨默斯说过,让进哈佛的每个学生都成才。哈佛大学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金子,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别,问题是让他们怎么发光。萨默斯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,他当新校长不久就有一个新学生来找他,说你是经济学家,应该注重每一个数据的准确性,我发现你的一个数据有错误。一个新学生敢向校长挑战,这就是哈佛的文化。难怪萨默斯说,如果哪一个大学能够有这种文化,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。普林斯顿大学,连续七年美国大学排名第一。哈佛大学过去三年曾和它并列第一,但最近一次又落于其后,原因在于普林斯顿大学有两个指标超过了哈佛大学。虽然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仅有6000多名学生,但是小学校拥有大文化,它可以接纳有精神病的纳什教授,没有让他下岗,这就是宽容文化 ——“美丽的心灵”。
文化对于学校非常重要。而我们很多大学欠缺着文化。不管是在哈佛大学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,谁都不代表真理,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;真理高于一切,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,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。所以,师生之间可以讨论,甚至争论。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,在与老师讨论中,也曾在争论中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。可第二天一大早,他的老师冯?卡门就告诉钱学森:你是对的,我是错误的。可中国的大学呢,从漫画的通常表现手法就能看出区别来:一定是老师在台上,老师显得很大,在中央;学生画得很小,在旁边;学生什么都不知道,一个个在问老师,老师什么都知道,他是发布真理的。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、宽容、不浮躁的学术环境,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。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。
除了“文化内涵”, 一所大学还要有良好的办学体制。
记者:一流大学要有有形资产、人力资源、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办学体制。您是否认为,除了有形资产外,其他三方面我们都很欠缺。
杨福家:现在国内大学软件、硬件建设失衡。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、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大有改善,其中很多建筑很豪华,甚至远超国外一流大学。此外,不少大学还都有好几个校区,且相隔甚远,不得不开班车,学生、教师大量时间浪费在路途上,这与当今先进办学理念背道而驰。同时,大学的软件建设则被忽视,大师、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方面相对欠缺,没有特色,没有文化内涵。笔者到过国内很多大学城,参观了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,但感觉不太好,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,看到的只是漂亮、甚至于豪华的建筑,但却没有人气。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,主要是观念和体制造成的缺陷。在观念上,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,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;在体制上,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。当前,教育存在问题的核心就是体制问题,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。
依法办学是关键
记者:那么,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?
杨福家:总结起来,关键是三句话:爱师爱生、依法办学、无为而治。
“爱师爱生”是常识,为什么要强调?因为如果没有一个“爱师爱生”的大环境,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,其它就很难做到。现在的问题是,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,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、科研成果,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,决定着他的待遇、名望和升迁。这能说是“爱师”吗?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就在于: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,每个人从进大学那天起,就有人关爱他。剑桥有一句导师的名言是:“我的烟熏将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。”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,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,而找到火种并且点燃,不光需要训练的技术,更需要爱。可是在国内,大学生和学校、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淡薄,这能说是“爱生”吗?“爱师爱生”不是空洞的说教,它与体制密切联系,不可分割,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,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。
记者:您所说的“依法办学”主要是指什么?
杨福家:作为现代大学,做事要有规范,要依法办事。法律包括宪法、教育法等,在这些法律基础上,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“宪法”,即大学的章程。其实,《高等教育法》早就明确规定,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。但是,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?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?要做到依法办事,大学首先要制订自己的章程,有了章程,依法办事,最后达到无为而治。老子最欣赏“无为而治”,使老百姓感受不到上面有一个统治者,这就是最好的统治。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,教育部就不必什么事情都亲自去管,而是放手让大学自己去做。唯一需要教育部做的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。
记者:爱师爱生、依法办学、无为而治这三个方面中,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。
杨福家:对,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“按法办事”。比如,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一百页,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。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,必须按法办事,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。
记者: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,即使有法也不依。
杨福家:我对此深有体会。我在国内有很多顾问的头衔,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,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,劈头就说,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政府的顾问了。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,我完全没有准备,市长一句话就给我戴上了“顾问”的帽子,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?毫无意义。但是,在依法办学的大学,顾问是有意义的。几年前,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特别顾问,我表示同意后不久,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寄给我一个文件,文件里规定了顾问的权利是什么,义务是什么,能做什么,不能做什么,都清清楚楚。我签字后,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。2005年,我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。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香港政府“大学资金委员会”的国际委员,这个委员会决定各个大学的经费分配,要求其成员不能与各大学有利益关系,所以,我必须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。而在内地,所有的顾问则都是“终身制”,不需要辞职。
记者:没有想到,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。
杨福家: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,而且非常清晰,我们的大学就缺少这样的规定。所以我认为,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,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。这样一来,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,这就是“自主办学”的含义。
记者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里有明确规定,各大学“自主办学”。遗憾的是,落实不了。
杨福家:怎么自主办学?不是来自个别人的恩赐,而是来自法律的授权。
记者: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,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,无法可依,一个是即使《高等教育法》里有规定,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。
杨福家:实际上,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批准,只有它没有违反法律就行。比如美国的教育部无权干预大学的事情,大学就是按照自己的章程去办。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,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,只要获得批准,大学就按照章程办事,除非违法,违法就根据法律处理。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,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。像美国的教育部,大门口有两句话“教育公平,教育质量”,这是它要管的事情。只有这样,大学才能做到“自主办学”,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——“民主办学”也是《高教法》里明确规定的。只是大家不太注意罢了。温家宝总理说,一所好的大学要有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。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?这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民主办学。
“表面上是尊重,实际上是贬低”
记者:2009年年初,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:“教育方针、教育体制、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,属于国家行为,应该由国家负责。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,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、校长负责。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,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。”由懂教育的人办学,这也是现在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,大家都在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。
杨福家: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世界范围内招聘,而不是由教育部来任命。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,把行政化色彩带到高校里,这是造成今天大学氛围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,表面上是尊重,实际上是贬低!在国外,大学校长绝对不是副部级,教育部部长都对他们很尊敬。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•盖茨以前就是一位大学校长,他接到国防部长任命后写了一封信说,我热爱这个学校,但是国家需要我,我更热爱我的国家,我必须走。韩国的一位大学校长直接被任命为总理。日元上的人物福泽喻吉就是庆应大学的校长,并非王室成员。
记者:看来,把校长定位副部级,表面是抬高,实际上不过是明确把大学校长定位为教育部的下属,校长与教育部之间定位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
杨福家: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,哈佛校长不见他的,为什么要见呢?没有一个校长会见他。英国的教育部长是内阁成员,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,我会会见他,但这是礼节性的,表示对他的尊重,可是他说任何的话,对我没有影响,更不意味着他的话就是“指示”,我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。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“指示”,他知道自己的地位。诺丁汉大学有一个15层的高楼,建在路边,很不合理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,也建议拆掉。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决定,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,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。撒切尔夫人的的话我们可以听,但是我们不一定按照去做,她也不会追究“你怎么没听我的话”。因为学校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,政府是政府,学校是学校。
记者:但是,中国却把大学视为政府的附庸,教育部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是自己的下属。
杨福家: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,但是去除大学的行政化是应该的,至少应该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时候,那时大学没有行政级别,不管是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,还是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,他们的地位都非常高,绝对是高于部长级的。
记者:核心的问题是要保证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,它和政府之间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,政府做什么,学校做什么,大家都非常清楚,而不是说学校是政府的一个附属。
杨福家: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并不意味着一所大学可以为所欲为,它要在法律下运作,不能违法。
记者:教育家需要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。在您看来,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,换句话说,教育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?
杨福家:作为一个教育家,第一,他应该了解世界的教育,也了解中国的国情,而且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。第二,他必须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,最好能够在教育系统学习过。
以前我讲过,美国的一些大学都有几百年历史了,像哈佛已经373年,比美国历史还要长。中国的大学才多少年,怎么和人家比?但是我现在的观点变了。16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接待过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。当时,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:“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。其领土的60%是沙漠,90%是干旱地。但我们是农业强国,高科技强国。”我问:“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?”他答了一句:“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。”以色列最早的大学是1924年才建立的,不到 90年就有了7所一流大学。近年来,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。论土地面积,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;论人口,上海是以色列的3倍;论环境,我们60年和平,他们战火不断;论历史,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,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,却没有一所可与以色列那7所大学相比!60年过去了,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?对比这些,对中国教育现状怎么会没有危机感呢?
记者:在美国,历史不到100年就成为世界名校的也有,关键是大学怎么办。
杨福家:新中国成立60年了,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。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已经有七位了,但是他们与新中国的教育没有任何关系。例如,杨振宁和李政道是解放前的西安联大时期培养的。
记者:西安联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,虽然那时候很穷,但是,它那会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了。
杨福家:包括谈家桢、苏步青等人的重要的学术文章,都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,因为那个环境允许搞学术,而现在的环境呢,使学者浮躁得不得了。最近我在几次演讲中,都要求取消研究生毕业要发表几篇SCI文章的规定。如果把这个规定用到世界上,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拿不到学位。很多获奖者就是靠他们的博士论文,此外就没有其他文章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求至少发表两篇,这不是很荒唐吗?
我们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,把关系理顺了,大学就会发展很快,就会出很多人才,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老出不了人才。使人满意的体制应该能够保证大学由教育家办学,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,自由的表达办学自主权,保证做到《高教法》规定的“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,依法自主办学,实行民主管理。”
大学绝对不能盈利
记者:根据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校长期间的观察,对比国内大学,英国大学运作的特点有哪些?
杨福家:我曾经问过哈佛大学校长,他说在美国大学校长主要做两件事:全世界找钱、全世界找人。最早诺丁汉大学找到我时,我首先去问,我要不要去筹钱呢,弄钱我可没有手段。后来我才了解到,与中国一样,英国的学校都是政府的,不需要校长去弄钱。实际上领导学校的是三个委员会:校务委员会、教务委员会、学术委员会,在三个委员会之下有一个执行者,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,这个执行者就相当于国内的校长。教育部不干预学校的事务,各大学都依法办事。在就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半年以后,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,我发表了一次演说,直言英国的大学可以与美国大学竞争,但是永远超不过美国。为什么呢?因为美国大学要自己筹集资金,重要的还不在于钱,而在于社会是否认可大学,只有得到社会认可的大学才能获得社会的资助,这激励着美国大学都奋力追求卓越。办好大学的第一个条件,就是看它能不能够拿到非政府的资助,非政府的资助说明社会的一种认可。
记者:现在国内民众普遍对教育不满意,大学很难得到非政府的资助。
杨福家:老百姓对教育不满意,怎么会给你钱?而在美国,来自非政府的资助可以让教授安心研究,不要考虑生活问题。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全心全意在搞学术研究?包括学生,高中生不念书了,为了找工作,大学生最近几年也不念书了,教学质量怎么会高啊?我才不相信呢。
记者:中国大学也在搞市场经济,许多人都在困惑,大学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?
杨福家:大学校长、科学家与总经理绝对不能混在一起,这三者是个三角形,要搞科研,就专心搞科研,既要搞科研又要做大学校长,做不好的;要做生意,就专心做生意,既要搞学校管理又要做生意赚钱,也不可能做好。我做复旦大学校长的时候就讲,学校的责任不在于拥有多少家公司。我一直反对学校办公司,但是学校一定要为经济服务。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,有人统计过,美国经济增长有70%来自大学。大学必须对经济发展有贡献,但这不等于大学一定要办公司。
记者:大学应该对经济有贡献,并不等于大学就要办公司。
杨福家:大学不能办公司。大学可以抚育公司,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占有公司。麻省理工学院抚育出多少公司,可是自己没有一个公司。所以必须明确,在现代社会,大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是责无旁贷的,必须为经济服务,但是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与经济直接有关系的工作。这是两码事。一定要有一部分人做长远的基础性的研究,做他们有兴趣的研究,即使与经济毫无关系,也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研究条件,让他们安心工作。
记者:如果说大学和政府之间要有清晰地边界,同样大学和市场之间也要有清晰界限。
杨福家:我一开始就反对“教育产业化”,因为大学是一个公益的事业,绝不能有任何盈利。即使因为某种原因有一点收入,这些收入只不过是总收入的一部分,应该用于增加教学研究经费。绝对不能与教师的利益挂钩,教师的工资应该由学校来出,要保证他们安心工作,全力以赴,同学随时可以找到他们。可是现在国内大学教授兼职之风盛行,北京有一所大学的一位研究生,已经毕业了,他说老师的面都没见过!当然,教授也有他们的苦衷,学校里发的那点工资不能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生活。这样子,中国教育搞得好吗?
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
记者:对于现在大学实行的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,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,认为应该改革,您的意见呢?
杨福家:对于这样的领导体制暂时不要动,因为这是《高教法》里规定了的。但是一定要厘清,什么是“党委领导”?不是党委书记领导,而是党委集体领导。
记者:问题是,在实践中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往往会蜕变成为“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,所谓集体领导最后往往变成一个人领导。
杨福家:确实如此。许多大学的党委会基本不开,即使开会,尽管党委书记只不过是委员会中间的一个,可是委员会其他成员敢讲一句与他不一样的话吗?常委会上,党委书记说了算。所以,我主张,要在现行的体制下改造党委会。
记者:党委会要改造成什么?
杨福家: 党委会成员至少有三分之一由教授中选出。什么叫“教授治校”?重点是有一套体制保证:教授,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授受到充分的尊重;他们在学校内有充分的发言权与决策权。教授不一定要当官,但是教授一定要有发言权,教授在学校里最受人尊敬。在我们诺丁汉大学,教授绝对有权,表现在哪里?如果校长做得不好,30个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有8名成员认为校长不合格,就会启动一个程序组织调查,而不是说通过教育部的程序来做,因为人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学术自治体。换校长要组成12人委员会,6个人是第一线的教授,还有6个人是具有教育经验、与学校没利害关系的校外人士,而所有管理层是不能进12人委员会的,包括现任校长。所以,校长是教授选出来的,必须对教授会负责,如果你不代表他们讲话,党委书记讲什么你就听什么,下次就不选你了。我认为,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这种做法,党委会有三分之一时校外人士,三分之一是教授党员、学生党员选出来的,三分之一是学校领导层的负责人。
记者:这个方式不错,至少可以防止集体领导走样变成一个人领导。
杨福家:党委书记只不过是组织中的一员,而且要明确规定他的职权在哪里。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所中外合作办的大学,由英国诺丁汉大学负责日常教学,我提出来非要有党委不可。为什么?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党委是不行的,那么,党委干什么?第一,保证中国法律在学校里贯彻实施,监督学校不能违法;第二,在学校事务与政府发生关系的时候,党委去协调;第三,党委负责学生的思想工作,保证学校的稳定。但是学校的人事,党委不管,而是由校委会来讨论决定。经过改造,就可能真正做到“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”。
记者:党委领导,校长负责。如果真正改造了,其实这样的体制也是可以的。
杨福家: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。诺丁汉大学的“学校委员会”的领导不是校长,我是董事会的主席,我参加校务委员会,名单上我是第一个,但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是我,主席是校外的人士担任。我再举一个例子,我是执行校长,一个人执行不过来,任命了7 个副校长帮助执行。校长权力大得很,今天任命你,明天就可以解雇你,不要任何人批准。但是三个委员会盯着你,多少眼睛看着你,谁敢乱来?把亲戚拉来做副校长?那是根本不可能的,马上会有人提议弹劾你。校长有权力任命副校长,但是有两个人不能任命:财务长和教务长。执行校长是校委会选举的,财务长也是由校务委员选举的,然后推荐给校董会任命。还有管教学质量控制的教务长也是校务委员会选举的。
记者:校长、财务长、教务长三者是平行的。
杨福家:质量控制不在校长手里,财务权也不在校长手里。不像内地大学的财务长,如果不听党委书记或校长的话,马上就会被换掉。可是在诺丁汉大学,财务长工资很高,依法办事,只要他不违法,校长拿他没办法,因为他对校务委员会负责。教务长也是如此,哪像我们这里,一切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,尤其是财务都捏在手中,权力集中,当然容易滋生腐败。
记者:诺丁汉大学的这套机制设计非常科学。
杨福家:但是,中国大学负责人都要教育部任命,既然我是教育部任命,我为什么要听教授的?
记者:您的观点给我启发非常大,如果真的把党委会改造了一下,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改良措施,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。
杨福家:总之,高等教育必须改革。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十分必要。但是也很有难度,所以,我主张中国拿出几个大学做试点,像南方科技大学可以算一家,宁波诺丁汉大学可以算一家,再从“985高校”里拿几个做改革试点。
记者: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大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体,自主办学,实现大学自治。
杨福家:也不能完全做到自治,因为上面还是有菩萨,但是希望改革,途径就是在几个学校试点,三年以后就可见分晓。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。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: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;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的思考、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;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,依法自主办学,实行民主管理。
记者:其实不单是教育改革,很多方面的改革,都有这样的问题,改革到一定程度,会发现碰到一个“天花板”,改不动了。
杨福家:这就要有比较英明的教育部长、比较英明的总理支持做下去。否则,结果就是使得现状继续下去,出不了杰出人才。
但是我相信,总有一天会改变的。